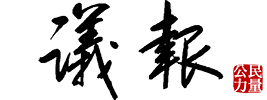石破天 | 见山书店:香港最后的告别
3月31日,香港独立书店上环见山书店,因不堪举报和投诉,正式结业。...
2024年4月16日
一路上,群众反响最强烈的口号,是那句“不要逼我造谣 ”。每当喊出这句口号,立刻赢得一片如潮如雷的掌声和欢呼。这就是所谓“不得人心的社会动乱”的真相,凡亲身经历过这个场面的人决不会搞错。游行队伍缓缓绕行广场一周,在人大会堂东边的马路上静坐了大约二十分钟,然后沿前门大街到新华社门前。大家齐声喊: “新华社,出来!新华社,出来!” 新华社大楼的窗口里,有不少人鼓掌,但没有人出来。一路上,群众反响最强烈的口号,是那句“不要逼我造谣 ”。每当喊出这句口号,立刻赢得一片如潮如雷的掌声和欢呼。这就是所谓 “不得人心的社会动乱”的真相,凡亲身经历过这个场面的人决不会搞错。我一直打着那幅“不要逼我造谣”的横标。一到家,我就把它牢牢钉在了客厅的墙上,窗外的过路人老远就能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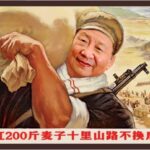
2024年4月15日

2024年4月14日

2024年4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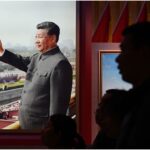
2024年4月11日
2024年4月9日
任何不重视保护公民社会免受中共干预的去风险战略都将是失败的。 来源:The Diplomat 作者:凯文•希夫斯(Kevin Sheives) 译者:撒母耳 (图片来源: Illustration...

2024年4月8日

2024年4月5日

2024年4月4日

2024年3月31日
2024年3月29日
来源:世界政治评论 worldpolitics review.com 2024年2月5日 作者:杂志编辑 译者:Fred 2021 年 4 月 25...

2024年3月28日

2024年3月18日

2024年3月17日
2024年4月4日
荷兰人权组织“罗斯福基金会”(Roosevelt Foundation)日前宣布,2024 年四大自由奖(Four Freedoms...

2024年3月19日

2024年3月4日

2024年3月4日
2024年3月17日
一个女大学生被逼自杀的故事揭示了当局对 “政治邪教”的打击。 来源:bitterwinter.org 《寒冬》陈涛、胡子墨报导 “走正道,行远路”夏令营学员表演(来自微博)...

2024年3月14日

2024年3月13日

2024年3月12日
2024年3月22日
题记:2019年,我有幸获得独立中文笔会第17届自由写作奖,评价中提及长篇纪实《丹麦人在安东》关注了丹麦传教士这一群体在历史变迁下的悲欢沉浮。去年,这部作品已由台湾新锐文创出版。中国作家冉云飞在《卌年...

2024年3月7日

2024年3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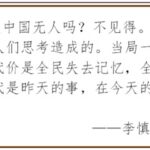
2024年3月2日
2024年3月26日
天堡城位于南京太平门外紫金山西峰,海拔267米,紫金山天文台附近,是太平天国时期修筑的一个军事要塞。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分别在紫金山西峰上下用巨石修筑了天堡城和地堡城两座坚固的堡垒,上下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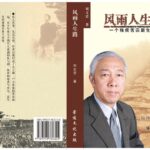
2024年3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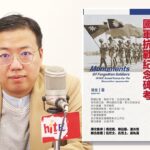
2024年3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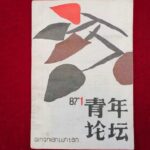
2024年2月18日
2024年3月3日 | 0
题图:2024年2月21日,在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门前,雨点滴落在簇拥于花丛中的纳瓦尔尼画像上。 来源:THE DIPLOMAT(2024.2.22) 作者:Yaqui Wang 译者:Erin...

2024年3月2日 |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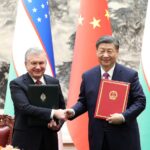
2024年2月23日 | 0

2024年2月21日 | 0

2024年2月19日 | 0
2024年3月18日 | 0
自2月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习近平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提法不仅写入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今年中国政府的首要工作任务,官方更是大造舆论,媒体和学者在铺天盖地讨论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把新质...

2024年3月12日 |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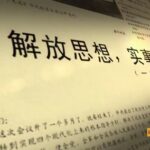
2024年3月10日 | 0

2024年3月7日 | 0

2024年3月1日 | 0
2024年3月7日 | 0
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共在潜在的台海危机未达到战争门槛时采取进攻性网络行动的方式。 来源:The Diplomat 作者:Seamus Boyle 译者:约书亚 Cred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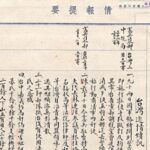
2024年2月11日 | 0

2024年2月10日 | 0

2024年1月18日 | 0

2024年1月15日 | 0
2024年3月2日 | 0
批评人士担心,在北京于 2020 年实施的法律基础上,当局将利用本地的国家安全法作为另一个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工具。 来源:The Diplomat 作者:Kanis Leung and Zen...

2023年7月9日 | 0

2023年3月22日 | 0

2023年2月9日 | 0

2023年1月4日 | 0
2024年2月14日 | 0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日前公布,该人权组织已荣获提名争取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这是继去年获提名的第二次。 今年的提名人包括:加拿大国会议员兼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 (SDIR) 副主席...

2024年1月14日 | 0


2023年12月27日 | 0

2023年12月14日 |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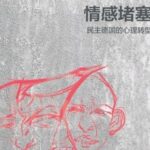
2024年2月27日

2024年2月21日

2024年2月15日